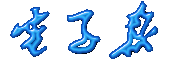苍树峭山间,白水亭下急,望远山归帆,似在云中现。
一幅丹青寄寓了画家多少内心的独白,挥毫拨墨,笔随意行,看似混沌,实则意味隽永。峭拔的山峰经历了岁月的洗礼,显得更加高大挺拔,站在它的脚下仰望,直干云霄,似乎只有它能够承担起擎天玉柱般的重任;苍劲的古树出现在山峰的每个角落,它们紧紧的依偎着山岩,像两个生死相依的生命,山有了树更显生气,树在山间更显活力;水是生命的源泉,是山的灵魂,一泓清泉流淌山间,时而叮咚作响,时而从高处直泄而下,湍流不息,为这里增添了灵动,为生命注入了血液。这里只有一种声音,那就是大自然的呼吸,看,那里有很多鱼在毫无顾忌的欢呼跳跃;听,远处高山上有人在歌唱,歌声悠扬飘渺;山顶的凉亭被古树环绕,郁郁葱葱,越过凉亭,眺望无边无际的江面,是那样平静,那样广阔。江面的几只帆船正满载而归,带着家人的希望和满满的幸福。这又何尝不是画家心底的呼唤!呼唤那份消失已久的宁静和平淡的幸福!
山峦层叠云水际,青树白溪茅舍边。桃花源水何处是?画中非画乃吾心。
这里刚刚被一场雨水洗涤,蓊蓊郁郁的古树活力焕发,青翠的枝叶遮盖了裸露的岩壁,却遮挡不住流淌的山涧,看哪,弯曲的山涧像是银色的眉黛点缀在山间,它没有李白笔下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磅礴气势,却有曲径通幽的静谧之美;它的脚下是让多少文人墨客向往的草屋茅舍,友人来访,唯有乌蓬小船可以通行,远离尘世的叨扰,好不快哉!眺望远处的山峦,在蒙蒙的薄雾中与天水相融,何处是山?何处是我?何处是云?何处是水?只怕是早已融为一体了。
层山 远水
这里是山与水的世界,一望无际的山峦层层叠叠,分布在一条河的两边,像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这条南下的河流。看这些山,与树为一体,在薄雾的笼罩下,增添几分神秘。河流自北向南缓缓流动,偶尔突出的山岩似欲将河流拦腰横断,又像是仅仅开个玩笑,为穿越山川的河流增添几许妩媚。水是“上善”之物,又具有强大的力量,穿越在崇山峻岭之中让威武的山脉略显柔情,激荡在山间曲径为这里带来几分灵动。我们临江而立,眼前的山川层峦叠嶂,欲阻断我们远望的视线,却不能阻断我们心中的向往。
水墨丹心
这是画家石民岗的几幅作品,有限的文字难以倾尽画中深远的意境,只能做粗浅的解读。
“石民岗多才多艺,供职于铁路,却醉心于艺术。曾痴心书法,一手古意十足的章草享誉圈内,后染指绘画,同样显现出过人的领悟力。率性和才情皆备于他,于人则见风度,于画则成格调。”
“他的画以山水见著,作品构图立意高远,山色葱郁,山势挺拔,画面淡淡的云雾衬托,山川雄秀之美一览无余。山间漂浮的白云,山顶倾泻的瀑布,调剂着密实的画面,一种隐藏与自然深处的灵动之感呼之欲出。”
“《秋风染醉野人家》大胆落笔,细心收拾,逐步深入,反复皴擦点染,即注意疏密黑白的关系,又体现浓淡明暗的布局,恰当处理脉络结构的关系,从而升华了主题”;《疏烟淡日》用寥寥笔墨营造存在的意境,气韵的流动产生非凡的气势;《泉清人亦静》在微小处点睛,赋予画面生动质感。
“他的章草化古生新,让人眼前一亮,”而他“以书入画,‘圆转如篆,点捺如隶,牵丝萦带,缠绵连接’的章草特点,无不给其以启发。”
山水意境
“中国的水墨画有种禅宗式大彻大悟极端超前的审美意识。道家美术文化以表现生动活泼的自然美为动机,水墨画追求山气欲动,青天雨变化,气韵藏于笔墨,笔墨皆成气韵的画面,以极简的黑白两色表达韵味生动的自然物象,有一种‘大成若缺’的道家辩证思想在里面。”
在石民岗的山水画中,成山之高则远近不同,高下有别,成山之俊则水绕树葱,层层叠叠,成山之美则浓淡重彩,奇险兀立;水之柔,之动,之灵,之远,皆以留白凸显,或狭长而清泠,或浩荡湍急,或广袤宁静,意蕴隽永。着墨处风景清素淡雅,或骨法用笔气势雄浑,或应物象形空灵飘渺;留白处天水合一,物我相融,宁静而悠远。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尽显其中。好一场视觉盛宴!一饱眼福之余,似与圣贤对语,更带给我们灵魂深处“静”的洗礼。
“当绘画简约到纯粹水墨语言,而色彩沦为‘补笔墨之不足’的辅助地位时,则要求中国传统书画中的基本构成元素‘点、线’的质量,要厚重到‘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’的境界。故此书法的重要性地位也在中国画中彰显出来。由此而论,一个不懂书法,和一个对书法缺少研究的人,则无从谈画中国画。尤其是水墨山水画。其画也无论从内涵到形式,也仅仅是再简单不过脑残‘画’而已。离正真的绘画艺术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和九重天。所以,南山乐山先生在《南山画缋随笔》中说:担当和尚题画曰:‘若有一笔是画也非画,若无一笔是画亦非画。’”
山水画自六朝经隋唐,在工匠大师吴道子以墨笔挥写出疏体山水之后,诗人王维以“水墨渲淡”表现出“画中有诗”的辋川山水,开始出现了泼墨山水,在众多画家的笔下逐步形成了水墨山水的艺术语言。然而,经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,有人认为当下的山水画正面临着危机,黑格尔曾说:“拿来摆在当时人眼前和心灵前的东西必须也是属于当时人的东西,如果要使那东西能完全吸引住当时人的兴趣的话。”那么山水画将从何处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,在危机面前化险为夷?时代的需求或许是最好的导向。